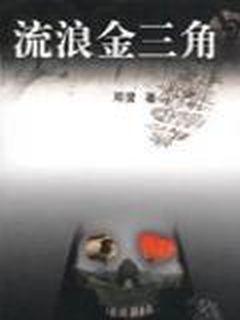- [ 免費 ] 第壹章:《歷史的禁區》 ...
- [ 免費 ] 第壹章:歷史的禁區
- [ 免費 ] 第二章:《走進金三角》 ...
- [ 免費 ] 第三章:《潘多拉魔盒》 ...
- [ 免費 ] 第四章:《鋌而走險》 ...
- [ 免費 ] 第五章:《背水壹戰》 ...
- [ 免費 ] 第六章:土司招親
- [ 免費 ] 第七章:封疆大吏
- [ 免費 ] 第八章:“反攻雲南!” ...
- [ 免費 ] 第九章:撣邦風雲
- [ 免費 ] 第十章:帝國神話
- [ 免費 ] 第十壹章:“旱季風暴” ...
- [ 免費 ] 第十二章:譎波詭雲
- [ 免費 ] 第十三章:大撤臺
- [ 免費 ] 第十四章:《兵燹》
- [ 免費 ] 第十五章:刀鋒相向
- [ 免費 ] 第十六章:危機四伏
- [ 免費 ] 第十七章:仰光槍聲
- [ 免費 ] 第十八章:兵車南行
- [ 免費 ] 第十九章:“湄公河之春” ...
- [ 免費 ] 第二十章:罌粟王國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末路英雄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龍蛇爭霸》 ...
- [ 免費 ] 第二十三章:坤沙出逃 ...
- [ 免費 ] 第二十四章:神秘滿星疊 ...
- [ 免費 ] 第二十五章:青春似血 ...
- [ 免費 ] 第二十六章:走向深淵 ...
- [ 免費 ] 第二十七章:靈與肉
- [ 免費 ] 第二十八章:知青火並 ...
- [ 免費 ] 第二十九章:理想之光 ...
- [ 免費 ] 第三十章:朝廷招安
- [ 免費 ] 第三十壹章:蕩寇誌
- [ 免費 ] 第三十二章:灰飛煙滅 ...
- [ 免費 ] 第三十三章:〈金三角之魂〉 ...
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AA+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
简
第八章:“反攻雲南!”
2024-4-24 20:40
1
許多老人都說,我出生前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怎樣壹個生機勃勃和萬眾歡騰的年代啊!壹提起那段日子,我父母的神情立刻變得年輕起來,因為那時候他們正好年輕,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年輕的日子誰不珍藏在心呢?
舊政權像昨天的太陽已經落下山去,新時代像初升的朝陽剛剛升起來,新舊交替的時代變革給年輕人帶來許多新的選擇,許多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人人都有機會改變自己,改變未來,在壹個給人帶來變化的年代,人人都因為充滿希望而朝氣蓬勃。
我壹位堂伯父說:“那時候,報紙天天都有勝利消息,廣播裏朝鮮戰場天天都在打勝仗,美國人變得跟兔子壹樣只會逃跑。解放軍進軍西藏,大剿匪,農村土改,鎮壓反革命等等。人人都在歡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大街上秧歌隊鑼鼓喧天,歡送青年到隊伍裏去。總之那是個火紅的年代,人人都有緊迫感,形勢逼人,時代像滾滾車輪,妳壹猶豫就掉隊了。”
我的嶽父,壹位享受離休待遇的老人,他的經歷更是大起大落。本來到美國留學的飛機票已經買好,因為聽從組織召喚(他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進步組織),毅然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轉而投身保衛城市和學校的鬥爭。後來他被分配到政法戰線工作,是我們這座城市裏資格最老的法官之壹。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從此命運壹落千丈,直到改革開放,經過種種努力才爭取來壹個離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的父親就顯得比較被動,他壹心只想當科學家,對政治不感興趣,我認為這起碼是覺悟不高的表現。父親說:“那時政府號召年輕人參軍,抗美援朝,學習文化。大學裏也招兵,不少同學上著課就不見了,原來是參軍走了。”
我問:“您為什麽不去參軍呢?那時候參軍多光榮,我們也好落個革命軍人的光榮出身呀。”
父親回答我:“要是我打仗死了,就什麽也沒有,現在至少我還留下妳們這幾個孩子呀。”
我說:“當時您大學畢業準備幹什麽呢?”
父親回憶說:“妳爺爺打來電報,要全家都到加拿大定居,後來沒有走成,我也跟著留下來。”
我心中掠過壹陣激動,原來我們險些就成為令人羨慕的海外華僑啊。我幾乎絕望地嚷起來:“當時您為什麽不走?爺爺不去,您壹個人走啊,拿出您當年背著家裏參加遠征軍到印度打仗的勇氣來。”
父親望著遠處說:“我回到妳爺爺的工廠做練習生。是妳爺爺決定的。”
父親辛勤工作壹輩子,歷經人生坎坷,八十年代以副教授職稱退休。我幾乎有些恨我的爺爺,是他老人家扼殺了父親和我們壹家人的光明前途。後來發生的事情我知道壹些,爺爺工廠沒能堅持多久,因為私有化很快被公有制進程取代,爺爺變成壹堆被稱為“股票”的廢紙擁有者。他老人家民國初年創辦中國“裕華”、“大華”紗廠,是著名的民族實業家,仙逝於1960年。
我美麗的母親在學生時代向往參軍,當壹名光榮的誌願軍或者解放軍的女文工團員。那時候她只有十七歲,還在成都華美高中念書,是那種充滿幻想的花季少女。她的不少女同學都因為走上革命道路,穿上軍裝,成為跳舞唱歌的文工團員然後嫁給首長,成了很有級別的高幹夫人。我說:“您為什麽沒有去實現自己夢想呢?依您的條件,走這條道路應該不成問題呀?”
母親有些害羞地笑笑說:“當時部隊到學校招文工團員,我記得很清楚,說是到廣州去。首長第壹個批準我,馬上就讓上車出發。我說我得回家說壹聲,我最放心不下妳外婆。結果這壹回家就再也沒有出來……都怪妳外公自私。他把我當成搖錢樹,當兵還搖什麽錢呢?”
我說:“您為什麽不反抗呢?白毛女都能反抗黃世仁,您還不能反抗壹個外公嗎?您壹反抗,我們這些後代不就走上另外壹條道路了嗎?”
母親嘆口氣說:“這都是命啊!女孩子,遲早要嫁人,反抗有什麽用?”
我覺得像母親這樣的資產階級小姐基本上沒有什麽希望,沒有反抗精神,也沒有革命理想和堅定信念。但是連她都有過突圍沖動並險些獲得成功,這說明革命形勢已經像春風壹樣深入人心催人奮進。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關於本世紀五十年代初壹個新政權建立時的精神面貌。國民黨舊政權的陰影正在消失,共產黨領導的新時代剛剛開始,年輕的共和國因為贏得大多數民眾擁護而生氣勃勃,兵強馬壯,顯示出敢於同壹切帝國主義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在這樣壹個年代,任何人復辟舊政權和反攻大陸的夢想都是註定要失敗的。
2
許多年前,我在雲南邊疆度過壹段漫長而且難以忘懷的知青歲月。那時候我們兵團知青分布在千裏邊防線上,壹手拿槍,壹手拿鋤,執行祖國賦予我們屯墾戍邊和接受再教育的光榮任務。我所在的團(後改為農場)地處中緬邊境,地名叫隴川,全縣人口不足萬人,以致於許多知青到了目的地他們的父母還沒有從地圖上找到那個叫隴川的小地方。
其實我們守衛的這片國土上還是出過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出過全國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女英雄徐學惠。八十年代以後的年輕人已經不大聽說這個名字,但是在五六十年代,這個名字幾乎婦孺皆知,其知名度與江姐、劉胡蘭、丁佑君、向秀麗等女先烈並列,惟壹的區別是先烈死了,徐學惠活著。
徐學惠是隴川縣銀行,準確說是我們農場壹個小儲蓄所營業員,那個小儲蓄所離我們連隊只有三裏地,在糖廠水庫邊上,而我們農場另壹個後來成了有名氣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們連隊也離那座水庫不遠。我們很多知青都到那個小儲蓄所存錢,不是錢用不完,是怕花光了回不了家。
徐學惠事件發生在五十年代的壹個夜晚,當時年輕的徐學惠只有不到二十歲,未婚,是否有對象不詳。壹群國民黨殘匪從國境對面的“洋人街”過來搶劫儲蓄所,徐學惠死死抱住錢箱不松手,以致於殘暴的匪徒竟把她的雙臂活活砍下來……
這是我們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隴川發生的著名事件,這件事甚至驚動當時的黨中央和毛主席。徐學惠出名後受到黨和國家關懷,調到昆明,裝上假肢到處給青少年作報告。“文革”期間受“四人幫”拉攏當上省革委副主任,相當於副省長,終於晚節不保銷聲匿跡。
當我在金三角采訪反攻雲南的國民黨殘軍,提及名噪壹時的徐學惠事件,他們都搖頭否認,不肯承認罪行,好像個個都很無辜的樣子。我理解他們的心情實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認南京大屠殺,好像那幾十萬人都是自殺的。徐學惠會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來嗎?
國境對面那個外國小鎮叫“洋人街”,據說是國民黨的據點,後來我才知道,“洋人街”是聯合國禁毒署列入名單的世界毒窩之壹。不過當時金三角惡名遠沒有像今天這樣令人談毒色變,政治任務高於壹切,所以我們屯墾戍邊的主要任務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蔣殘匪竄犯邊疆。
“蔣殘匪”是個定義不詳的歷史符號,從前我常常在電影中看到他們,就是那種經過藝術加工的獐頭鼠腦的壞人。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這個符號就變得很不具體,比方夜裏突然升起壹二顆信號彈,出現幾張反動傳單,傳說某地橋梁水庫遭到破壞,生產隊耕牛被毒死,等等。開始知青警惕性很高,深夜壹吹集合哨,大家趕緊起床執行任務,褲子穿反也顧不得,壹心指望抓住敵人當英雄,有人因此掉進溝裏摔斷腿終身殘廢。久而久之,白天勞動,晚上備戰,人累垮了,敵人卻連鬼影也沒有見壹個。幸好後來上級傳達指示,說敵人搞疲勞戰術,我們從此安心睡覺不再理會。
我們勞動的山坡對面就是今天令人談毒色變的金三角,國界是壹條不足兩米寬的小河溝,兩邊山頭上都覆蓋著郁郁蔥蔥的森林。我們男知青常常站成壹排,壹齊把尿撒過國界,戲稱“轟炸金三角”。“洋人街”坐落在我們連隊對面山上,肉眼能看見許多鐵皮房子掩映在綠樹叢中,太陽壹升起來,那些房頂就閃閃發光,像小時候看過的童話故事,令人遐想無限。但是指導員嚴肅指出,殘害徐學惠的國民黨殘匪就是那裏派出來的。敵人亡我之心不死,他們每時每刻都在企圖復辟,妄想反攻大陸。還鄉團回來了,我們就會千百萬人頭落地!
邊疆七年,我的知青生活中像風壹樣刮過許多有關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傳說。比方五十年代,某寨子吊死我兩名英勇的偵察員。某路口,敵人支起大鍋將我方傷員(或者幹部,或者農會主席)活活煮死。我沒有想到的是,許多年以後自己將走進這些躲在金三角也就是歷史帷幕後面的人群中間,成為壹段特殊歷史的揭秘者和書記員。
另壹件事情是,八十年代末我重返農場,改革開放,邊疆發展邊貿,我終於有機會走進國境對面那座像乩語壹樣神秘邪惡的“洋人街”,了卻壹樁心願。其實我看到這是座很平常的緬甸小鎮,低矮的鐵皮屋頂,飛舞著蚊蟲蒼蠅,充斥著垃圾和熱帶氣息的骯臟街道,做生意的人群和騾馬散發出令人惡心的汗酸味,毒販公開向遊客兜售毒品。在壹座大房子跟前,當地人告訴我,這是從前的漢人(國民黨)情報站,廢棄多年,現在成了教堂。我駐足傾聽,果然聽見有嗚嗚呀呀的管風琴聲從教堂的窗口飄出來。
我重重舒壹口氣,走出歷史陰影,走到明亮的陽光下。
3
許多金三角老人回憶說,1951年,反攻命令壹下達,在國民黨官兵中引起壹片熱烈歡呼。許多人流出激動的眼淚,對空鳴槍,扔帽子,還有人幹脆蹲在地下嚎啕大哭,好像壹群被告之可能回家的流浪孩子。
我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曾經對此深感困惑。因為我不明白,這些丟盔卸甲的國民黨殘軍難道沒有壹點自知之明,他們憑什麽相信反攻大陸會成功?他們難道忘記僅僅壹年前,他們是怎樣從大陸狼狽逃出來的?他們難道真的不知道他們的對手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強大,而他們自己不過是壹群虛張聲勢的流寇?
但是當我走進五十年前這群失敗者中間,我的心情豁然開朗,因為我並不費力就找到答案所在。
在泰國北部城市清萊,壹位參加過反攻雲南的前國民黨將軍面對來訪的大陸作家,極為感慨地嘆息道:“我們同共產黨打了幾十年仗,還是不了解共產黨。現在來看,反攻大陸完全是壹廂情願的事,因為我們根本不了解大陸,總認為人民站在我們壹邊。如果人民站在我們壹邊,國民黨怎麽會失敗呢?……弄明白這個簡單道理,我們用了五十年時間。”
在金三角小鎮回海,另壹位已經加入泰國籍的華僑老人平靜地說:“什麽叫鴻溝,什麽叫仇恨?國民黨被趕出大陸,趕出國境,這叫仇恨。廣大官兵只能聽見臺灣宣傳,相信壹面之辭,這是鴻溝。臺灣宣傳說,共產黨如何殘暴,屠殺人民,共產共妻,老百姓怎樣生靈塗炭,人民如何盼望國軍回去解救他們,只要妳們反共救國軍壹到,人民立即就會群起響應,以起義和戰鬥歡迎妳們,共產黨政權立刻就會像太陽下的冰雪壹樣土崩瓦解……妳知道蔡鍔北伐的故事,他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我們把李主席看作金三角的蔡鍔,反攻雲南就是又壹次北伐。如果我們有可能像現在這樣常回大陸看看,誰還會相信那些幼稚可笑的政治謊言呢?問題在於,當時我們都相信了,而且深信不疑。”
我感興趣的另壹個問題是,如果廣大官兵被蒙蔽,作為國民黨主帥的李彌,他相信自己會成為壹個新的蔡鍔麽?他有能力改變歷史命運,反攻大陸成功麽?如果他不相信,他為什麽還是要全力啟動這場大陸解放以來惟壹壹次大規模竄犯大陸的軍事行動?他怎樣扮演這個兩難的歷史角色?
根據不少老人的敘述,我漸漸看見將近半個世紀前,反攻雲南的國民黨主力在孟薩集結完畢,李彌親自將部下兵分兩路:壹路大張旗鼓向東佯攻景洪,擾亂共軍視線,另壹路主力則在緬北山區隱蔽行軍,直到四月下旬才抵達壹座地名叫做巖城的佤山。巖城古稱永恩,界河對面就是雲南西盟縣城。
我對此感到疑竇叢生。作為壹個軍事指揮官,“兵貴神速”永遠是壹條戰術要義。可是李彌部隊似乎並沒有緊迫感,他們就像遊山玩水,幾百裏路居然走了兩個月時間。我向武老請教,前國民黨幕僚回答說:“行軍就是行軍,沒有人拖延時間。”
我攤開地圖向他指出:“可是這樣壹條路線,妳們居然走了整整兩個月!那麽妳們都幹些什麽事情?”
他態度甚為安詳地說:“發動群眾,擴大影響呀!我們每到壹個地方,就動員青年當兵,建立反共遊擊武裝,宣傳三民主義等等。”
我說:“妳們不怕暴露意圖,不怕解放軍偵察到妳們行蹤?”
武老笑笑說:“只有傻瓜才會相信,我們那區區幾千人能反攻雲南。美國人在韓戰中吃緊,臺灣有精兵百萬尚難自保,我們能起多少作用?”
我眼睛壹亮,追問道:“李彌真是這樣想的嗎?既然明知道不可為,為什麽還要反攻雲南?”
武老點頭贊嘆道:“這就是李主席英明過人之處啊!古人雲,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嘛。”
我開始有些明白,李彌其實是在下賭註,只不過他押的寶不在大陸,也不在臺灣,而在美國人身上。
緬北山區原本沒有國民黨勢力,李彌大軍壹路走,壹路招兵買馬,幾乎毫不費力就把沿途土司山官統統招安,封了許多縱隊司令支隊司令,最小的也是上校獨立大隊長,反正只要給槍給錢,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部落酋長封建頭人決沒有不肯依附的道理。李彌對此很滿意,向臺灣發電稱,反共救國軍實力擴大好幾倍。
巖城是座方圓百裏的大山,為佤族山官屈鴻齋的領地。屈鴻齋號稱“巖城王”,這個土皇帝卻不是佤族,他是雲南漢人,犯殺人罪逃過國境避難,做了佤族山官的上門女婿。山官沒有兒子,由他繼承世襲領地。李彌派人做策反工作,送了許多銀元和槍支,委任他為少將縱隊司令。事實上這種收買戰術幾乎百戰百勝,比如從前的殺人通緝犯屈鴻齋,壹夜之間舊貌換新顏,坐在家裏就白白當上將軍,這樣的好事上哪裏去找?山大王屈鴻齋簡直被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砸昏了頭,立刻豎起反共救國軍旗幟,積極充當反攻大陸的前鋒。
4月,擔任佯攻的部隊來電告急,說共軍主力來勢兇猛,隊伍被黏住撤不下來,如不及時撤退,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也就是說,李彌在路上慢騰騰地磨蹭,反攻大陸的計劃尚未執行就有可能流產,這樣至少沒法對臺灣交差。當然還有壹個更加重要和隱秘的原因,這是李彌全部計劃的核心,如果反攻流產將危及這個計劃的實施,所以李彌突然變得著急起來,倉促變更部署下達命令。
前衛師長李國輝奉命淩晨向滄源縣城發起進攻。
4
這是個久旱無雨的黎明,雲貴高原的紅土地因為缺乏水分而變得蒼老,壹層薄霧如碳灰般將天地籠罩,河流奄奄壹息,巖石蒙上壹層灰。在這個霧蒙蒙的背景下遠遠望去,巨大的朝日剛剛升起,好像壹枚被踩扁的紅鴨蛋,坐落在山巒間的滄源壩子猶如涸轍之鮒,張開幹渴的大嘴等待壹天漫長的熱帶幹風和太陽的無情煎熬。
在這個旱季即將走到盡頭的早晨,國民黨先遣部隊越過國境線,對滄源縣的前哨陣地蠻宋發起攻擊。解放軍駐蠻宋壹個排,以石頭碉堡的哨所為陣地進行頑強抵抗,戰鬥隨即展開。錢運周指揮特務大隊和士兵將哨所團團包圍,雖然國民黨官兵都知道共軍只有壹個排,等於壹顆釘子,而不是匕首,但是他們的行動還是十分小心謹慎。因為這裏畢竟是大陸,對手不是只會朝天放槍的老緬兵土司兵,誰能說釘子不能致人死命呢?
青黑色的碉堡像壹頭怪獸,披著壹層淡薄的晨霧蹲在山坡上,黑洞洞的槍眼猶如深不可測的眼睛,讓人感到心驚肉跳。壹群色彩斑斕的印度虎皮鸚鵡被士兵腳步驚飛起來,它們在亞熱帶旱季幹燥的空氣中努力振動翅膀,把誇張和不安的尖叫聲撒得很遠。錢運周從望遠鏡裏看見碉堡外圍有許多障礙物,樹叢中有新掘的戰壕,解放軍隱蔽得很好,看不見人影晃動。
碉堡越來越近,只剩下幾百米距離,敵人還是沒有動靜。錢運周感到背上有些發冷,這是壹場正規戰,不是打土匪,作戰雙方是較量幾十年的老對手,彼此熟悉得如壹家人。共軍好像有意折磨他們,越是保持沈默,進攻者越是緊張,誰都知道,距離越近,打得越準,國民黨士兵快把頭埋在地上,雖說敵人只有壹個排人,可是槍響起來,誰又擔保自己腦袋不被先打穿幾個窟窿呢?……
終於“砰”的壹響,共軍開槍了!槍聲使人精神壹振,快要凝固的空氣嘩啦破碎了。這壹槍實在太差,像走火,因為子彈並沒有射向人體,而是滴溜溜地鉆進泥土裏去了。所有人都同時松了壹口氣,就像捆綁在身上的繩索松開來,他們從地上擡起頭來張望,看見解放軍陣地上冒出壹縷細細的青煙,可以想象那是個驚慌失措的新兵。於是進攻壹方士氣大振,嗷嗷叫著兇狠地彎腰沖鋒。
形勢對防守壹方不利,盡管他們頑強抵抗,但是雙方畢竟力量懸殊太大,所以第壹輪進攻下來,國民黨殘軍占領外圍陣地,把剩下的解放軍全都逼進碉堡裏去了。
晨霧漸漸散開去,太陽露出臉來,把紅通通的光輝斜灑在戰場上。碉堡四周躺著幾具屍體,他們看上去不大像死人,臉上泛著紅光,像心滿意足的醉漢。錢運周讓士兵喊話,繳槍不殺,國軍優待俘虜,碉堡裏面有人大聲回罵。這時李國輝也上來了,他聽出對方是個河南口音,就對錢運周苦笑道:“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媽的!給我轟老鄉幾炮!”
炮聲壹響,對方沈默下來,解放軍當然明白炮擊對他們意味著什麽。炮彈將不結實的碉堡掀開壹角,石墻炸塌,壹些殘肢斷體被氣浪血淋淋地拋到陣地外面來。國民黨官兵歡呼起來,他們被勝利的炮火所鼓舞,挺直腰來進攻,解放軍這回是真的完蛋了,好比壹頭死老虎,誰先沖上去誰揀勝利果實。
頑強的解放軍還有壹挺機槍在廢墟中射擊,零落的步槍也向進攻者表達誓死不降的決心,進攻人群吶喊著,像潮水壹樣撲向孤零零的石頭碉堡。這是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勝利眼看就要得手,敵人馬上就要被全殲,反攻大陸首戰告捷的電報立刻就要飛向臺灣,國民黨打了許多年敗仗,逢共必敗,這回他們要向老對手劃壹個精彩的句號。但是這時候壹個意外發生了,他們身後突然飛來壹陣劈頭蓋腦的手榴彈,就像晴空萬裏下起冰雹,手榴彈的猛烈爆炸打亂進攻的隊伍,連督戰的李國輝也險些被壹塊彈片擊中。
壹臺精彩救援的好戲就在國民黨反攻大軍眼前搶先上演。大約壹百多名機動靈活的解放軍援兵(其中部分民兵)從側翼發起虛張聲勢的襲擊,壹下子將敵人打懵了頭,與此同時,困在碉堡裏的解放軍迅速撤下陣地突圍。他們配合得十分默契,壹進壹退,壹張壹弛,就像給國民黨官兵上軍事課壹樣。
李國輝眼睜睜看著共軍像孫悟空壹樣逃出他的手心,這壹仗打得無比窩囊,煮熟的鴨子居然在他面前飛走了。他咬牙切齒地說:“給我追上去,壹直追進縣城。小錢,妳帶壹團人繞過縣城,切斷敵人退路。我要看看共軍再耍什麽花招!”
解放軍並沒有如李國輝所料那樣死守待援,他們在退路被切斷之前主動放棄縣城,朝雙江方向撤退。國民黨軍隊占領滄源縣城,俘虜部分未及撤退的傷兵、民兵和工作隊員。李彌聞訊大喜,迫不及待向臺灣發出戰場告捷電,報告反攻雲南首戰大捷,消滅共軍多少多少,已經切實占領雲南第壹座縣城滄源。雲雲。
5
五十年前的滄源是座只有幾千人口的滇西小縣,不通汽車,所謂縣城也就跟內地壹個小鎮差不多,除縣政府臨時辦公的幾間平房,其余都是民居。七十年代我曾經到過滄源,那時我眼中的小縣城僅有壹家國營百貨商店,壹家國營食堂,壹個小郵電所,和壹條石板鋪成的簡陋街道。聽說九十年代滄源徹底改變面貌,縣城擴大十倍,柏油公路壹直通到省城昆明。
1951年春天,所有重返雲南的國民黨官兵都為勝利欣喜若狂,李彌宣布在縣城舉行壹場慶祝“光復”儀式,他迫不及待地騎著馬,帶領壹群幕僚和臺灣記者越過國境,意氣風發地開進滄源縣城。長官檢閱了入城部隊,國民黨官兵舉行分列式和閱兵式,喊了許多參差不齊的口號,可惜當地居民甚少,因為打仗又逃掉壹些,所以掌聲稀落無人喝彩。
臺灣記者進行采訪,許多官兵流下激動的眼淚,他們說早就盼望反攻這壹天,我們壹定要打到昆明去,打到南京去,光復整個大陸。記者把這些豪言壯語都記在本子上,用電臺發回臺灣,還附上傳真照片,說明國軍官兵士氣高昂所向披靡。
李彌視察縣城時險些被壹發偷襲的子彈擊中,他身後壹個幕僚做了替死鬼,原來是滄源縣民兵大隊還在山上抵抗。民兵大隊長是號稱“巖帥王”的當地佤族山官田興武,他同時還擔任共產黨滄源縣長,本來經過秘密策反,田興武已經答應裏應外合消滅共軍,不料戰鬥打響,他又出爾反爾站在共軍壹邊戰鬥。李彌很惱火,叫“巖帥王”的親戚“巖城王”去招降,這才弄明白佤族山官有顧慮,怕國民黨不成氣候,搞不好落個雞飛蛋打的下場。於是李彌決定放下架子,親自同田興武談話。可憐佤族山官壹輩子沒有見過比團長更大的漢人軍官,他甚至連壹百公裏外的臨滄城也沒有去過,所以當大名鼎鼎的國民黨省主席親自同他談話,這位立場不穩的山官嚇得連漢話也說不清楚,結結巴巴像個小學生。他本是個世襲的部落首領,被中國歷史劇變的潮流所挾裹,身不由己地卷入階級鬥爭的激流旋渦中,所以他就沒法不像個陀螺壹樣左右搖擺。李彌當然看出田興武不是個人物,他只用了不出壹袋煙工夫就說服他倒向國民黨壹邊。李彌當場委任他為上校支隊長,然後將他和他的四百多個佤族民兵派到戰場去打頭陣。
俘虜沒有得到寬大。他們多數是工作隊員,有人負了傷,打著赤腳,還有壹個女俘虜,很年輕,戴著眼鏡,據說是大城市來的大學生。他們來不及跟上部隊撤退,也沒有戰鬥經驗,對於階級鬥爭的嚴酷性估計不足,因此他們成為這些反攻倒算的國民黨同胞的復仇對象。我在滄源采訪曾聽當地人控訴國民黨令人發指的暴行,其中最驚心動魄的壹件,就是這些滅絕人性的國民黨匪徒在滄源城裏支起大鍋,將水燒開,把俘虜和傷兵扔下鍋去煮。當時的情形不難想象,開水翻滾著,冒著滋滋的水蒸氣,許多人圍觀,發出快樂和滿足的哄笑,俘虜捆得像粽子,但是那不是粽子,是活人,女大學生!這幅殘酷的畫面壹直留在我的腦子裏揮之不去,我曾為那位不知名的女大學生的悲慘命運暗暗揪心,悄悄垂淚。後來我在金三角質問當時參加反攻的國民黨官兵:“妳們這樣做,不是跟日本人差不多嗎?”
他們回答:“對不起,我保證我所在的部隊沒有發生這種暴行……槍斃俘虜的事是有的,但是煮活人沒有聽說過。”
我氣憤地說:“難道是別人造謠,誣陷妳們不成?”
他們安靜回答:“可能因為仇恨太深,彼此都會有壹些過激言論和誤解。”
這回輪到我無話可說。我只好問:“現在……還有仇恨嗎?”
他們搖頭說:“都是中國人,過去的事想來很內疚。不管什麽黨,只要妳把國家治好,中國強大,我們就擁護妳。”
反攻滄源的初步勝利鼓舞了李彌,他下令乘勝進軍,壹路由李國輝率師進攻耿馬和雙江,另壹路由錢運周指揮進攻西盟和瀾滄,起側翼屏護作用。“巖帥王”田興武決心將功折罪,帶領他的民兵沖在前面打頭陣,解放軍兵力薄弱,連連後退,滇西防線很快被擊破。國民黨殘軍相繼占領四座縣城,並在城頭升起青天白日旗幟。這時大批守候在境外的馬幫蜂擁而至,他們像螞蟻搬家壹樣把這些小縣城裏可憐的百貨商店、儲蓄所、糧站以及壹切可以搬走的財產馱上馬背,然後源源不斷地運往金三角。這種盛況在當地持續了壹段時間,絡繹不絕的馬幫很有耐心地將上述幾座縣城搬成空城。
對於兵敗大陸的臺灣國民黨來說,他們太需要勝利,太需要精神鼓舞了,勝利是壹道美味大餐,而他們是壹群饑不擇食的餓漢。於是臺灣島上所有報紙電臺壹齊歡呼滇西反攻的偉大勝利,好像他們明天就要返回南京壹樣。軍政要員頻頻發表講話,政工部門組織民眾上街遊行,商會財界出資募捐,經過壹番沸沸揚揚地炒作,李彌頓時身價倍增,從壹個坐冷板凳的光桿司令變成家喻戶曉的國軍英雄,他儼然成了共產黨的克星,戰無不勝的二戰名將蒙哥馬利或者巴頓將軍。
臺灣的勝利歡呼還有壹個苦心,那就是做出姿態給美國人看。當時美國人在朝鮮戰場陷入苦戰,巴不得看到共產黨後院起火天下大亂,如果李彌們壹路高歌挺進昆明,共產黨豈不是兩面受敵首尾不顧麽?朝鮮戰場的局面不是很快會發生變化麽?蔣介石這樣做等於提醒傲慢的美國佬:妳們與共產黨打仗離不開我們國民黨,離不開臺灣!
然而就在臺灣和美國盟軍期待李彌勝利捷報頻傳的時候,李彌卻下令反攻隊伍在耿馬縣城停住腳步,壹住就是三個月。
6
耿馬縣城以東四十公裏,有壹塊山間平地叫猛撒,因為是半山腰,沒有水源,所以也沒有人居住。據說知青到來前幾十年,這裏森林茂密,是動植物的樂園,後來遭遇大煉鋼鐵,再後來伐木開荒,到處成了梯田,水土流失嚴重。當時我的同學王仕陸被分配到猛撒農場插隊,番號是建設兵團第二師第八團,他興奮地告訴我,八團居然有座飛機場!我譏笑他,妳們八團知青回家探親不是可以乘飛機了嗎?他說是座報廢了的機場,野戰機場,也許還能起飛戰鬥機。我說莫非妳們八團的橡膠樹需要空軍保衛?他說妳別笑,都是真的。抗戰時期,美國盟軍為了保衛駝峰航線,對滇緬日軍實施有效打擊,曾在猛撒秘密修建了壹座簡易野戰機場。機場只有壹條砂石跑道,幾間簡易棚屋,僅供小型戰鬥機臨時起降。機場即將完工之際,太平洋傳來日軍投降的勝利消息,機場於是尚未啟用便荒蕪下來。後來我查閱史料,同學說得不差,基本上與歷史吻合。
1991年我為寫作《中國知青夢》專程到猛撒采訪,果然看見那座荒蕪的飛機場。機場平整如故,沒有樹,跑道上長滿荒草,像座天然的足球場。
但是當我的視線投向1951年春天,李彌命令他的反攻部隊停在耿馬、雙江壹線按兵不動時,我註意到他同時占領了這座廢機場。國民黨殘軍在廢機場四周布下重兵,我從軍事地圖上看見,李彌部隊的防衛重心事實上已經轉移到這座沒有人跡的廢機場。另壹個反常的現象是,他們的對手解放軍好像也睡著了,沒有反擊跡象,連民兵遊擊隊騷擾也時斷時續,有氣無力。這就有點像姜太公釣魚,人和魚彼此漫不經心,玩著讓外人看不懂的遊戲。根據偵察報告,解放軍壹個團已經撤退到臨滄,滇西方向沒有大部隊。還有情報說共產黨政府機關也開始向大理撤退。壹些將領和幕僚認為共軍主力被調到朝鮮戰場,後方空虛,正是長驅直入的大好機會,有人甚至樂觀預言,半個月收復昆明,打敗共產黨只是壹個時間問題。好像前途壹片光明,共軍不堪壹擊,需要的只是進攻。
李彌穩坐釣魚臺,不為人言所動,對大好形勢視而不見,根本不理睬部下的焦急心情。他安之若素,每天與幕僚品茗論道,談棋說畫,好像他不是來打仗,而是來遊山玩水壹樣。許多急於打回老家的國民黨軍官都沈不住氣,猜不透老長官葫蘆裏賣的什麽藥,連師長李國輝也蒙在鼓裏,跟別人壹樣幹著急。
糊裏糊塗過了十多天,壹個沒有月亮也沒有烏雲的夜晚,星星在天空閃爍,李彌走出他在耿馬縣城的指揮部,騎上心愛的東洋大白馬,率領壹行部下和隨從直奔猛撒機場。當他們翻過山坳,壹個前所未有的燦爛景象突然像銀河落九天壹樣展現在他們面前。黑夜沈沈,機場燃起熊熊火堆,將山間平地映得如同白晝。士兵戒備森嚴,騾馬集合待命,樹叢中隱蔽著大批民工。不久天空響起隆隆的馬達聲,壹架沒有國籍的美制飛機飛臨人們頭頂,這只黑色的巨鳥在天空低飛盤旋,沈重的呼吸響徹夜空。許多國民黨官兵歡呼雀躍,他們激動萬分,以為幾年前抗戰大反攻的輝煌場面將在猛撒重演:巨大的艙門打開,全副武裝的空降兵和坦克大炮源源不斷地從飛機肚子裏開出來。
可惜時過境遷,飛機只投下幾只降落傘就慌慌張張飛走了。人們找到這些掛在降落傘下面的木頭箱子,箱子裏躺著美國武器和彈藥。不管怎麽說,這也算個期待,美國人沒有來,但是美國武器來了,抗戰八年,大後方不就是靠著美國援助堅持下來的嗎?民工忙碌起來,馬幫將這些從天而降的大箱子分解開來,馱上牲口,然後運回金三角大本營孟薩去。當然這僅僅是個開始,此後兩個月,沒有國籍的神秘飛機常常夜間光臨猛撒機場,將各種各樣的作戰物資空投下來,有次還投下兩名美國情報軍官。值得壹提的是,這些武器大多是美軍二戰中使用過的槍炮,美國人用舊武器支援盟友也不是什麽新聞,何況是無償支援。
直到這時,軍官們開始省悟李彌肚子裏的算盤。有壹天錢運周對李國輝說:“什麽反攻大陸?我看叫做反攻臺灣,或者反攻美國更好。總指揮在同臺灣做交易,我們都是他的道具。”
李國輝嚇了壹跳,連忙制止他說:“老弟,咱們都是軍人,傳出去就是謀反罪。再說長官不依靠美國不行啊。”
錢運周嘆道:“師長,我敢打賭,咱們這輩子是不要指望打回老家了。妳沒見總指揮在積蓄他的家當麽?好容易積攢的家當舍得同共軍硬拼?……唉,反正當兵吃糧,脫了軍裝也餓不死,管他個鳥!”
錢運周的話不幸而言中。當隆隆作響的飛機將裝備壹個標準軍(三萬人)的美式裝備空投下來之後,李彌不是宣布挺進昆明而是立即撤退,將主力部隊從雙江和耿馬縣城撤到國境上,作出隨時準備退出國境的姿態。這真是壹場莫名其妙的戰爭,西線無戰事,大家好像彼此謙讓,而讓戰局以外的人摸不著頭腦。當臺灣和西方輿論大肆渲染勝利,把這場有名無實的反攻雲南炒得沸沸揚揚時,李彌卻讓他的隊伍躺在國境上睡大覺,而他自己為了保險,將指揮部先期撤過國境十公裏。這個謎壹直藏了許多年,直到我在金三角采訪,壹位老者才向我揭開這個謎底:美國要求臺灣開辟第二戰場,臺灣命令李彌反攻雲南,李彌則討價還價要求美國援助武器。最後達成秘密協議,美國人同意援助武器,但是有個先決條件,就是空投地點必須在中國境內,也就是說必須在李彌反攻雲南之後進行。
這場遊戲沒有輸家,各得其所。
戰爭演變成壹場曠日持久的對峙。戰場雙方隔著兩百公裏距離,好像在玩老鼠和貓的遊戲。解放軍稍有動靜,李彌就往後退,解放軍壹撤走,國民黨又恢復原來的態勢。幾個回合下來,大家似乎都在比賽耐性,這就很像壹場沒有裁判的拔河比賽,雙方都在拖延時間,等待對方耐心耗盡。
對峙第三個月,僵局終於被打破,解放軍突然以兩師兵力快速運動,國民黨殘軍本是驚弓之鳥,立即向後撤退。這時壹個更加驚人的情報傳來,令李彌不寒而栗。原來共產黨早已布下天羅地網,壹支神勇的精銳部隊已經神不知鬼不覺穿插到國民黨側翼潛伏起來,只等烏龜把頭伸出來,向前深入壹步,這支部隊立刻封鎖國境,切斷退路,形成關門打狗的局面。從前那些鼓吹反攻昆明的軍官幕僚此時背上出了壹身冷汗,他們暗自慶幸還是老長官英明,沒有利令智昏,否則他們全都做了共軍俘虜。反共救國軍火速撤過國境,為防萬壹,李彌還將總部退過薩爾溫江東岸。
只有不識時務的田興武屈鴻齋們沒能逃脫覆滅的命運。他們本來是部落民族,為歷史潮流挾裹,又為眼前利益誘惑,因此替漢人李彌做了擋箭牌和替死鬼。解放軍封鎖國境,他們像被蜥蜴扔掉的斷尾壹樣,被毫不留情地掃進歷史垃圾堆。
7月,朝鮮戰場傳來和談消息,李彌終於找到借口,迫不及待地下令撤退,於是反共救國軍壹路高奏凱歌喜氣洋洋返回大本營孟薩。李彌不僅收獲了美國援助,而且隊伍空前壯大,總兵力翻了壹倍。
7
1998年初冬的壹天,我踏上飛往雲南省會昆明的航班。揚聲器報告飛經西昌上空時,我突然記起將近半個世紀前那個黑色的清晨,李彌從西昌機場起飛去與他的部隊匯合,但是失敗的命運無情阻斷了他的希望。這位國民黨將軍無法在大陸任何壹處機場降落所以只好只身飛往臺灣。我從壹萬米高空鳥瞰大地,紅土高原像壹只制作粗糙的沙盤躺在我腳下,這只古老沙盤已經存在了億萬年,而我乘坐的飛機則像壹只渺小的流星,在永恒的時間和空間緯度上匆匆劃過。
我的采訪是從原昆明軍區離休幹部李老開始的。1951年李老職務為軍區作戰參謀,參加過制定圍殲國民黨反共救國軍的全部作戰計劃。
“……年初軍區有情報,境外國民黨殘部可能對邊疆地區進行大規模竄犯。到三月下旬,敵情就陸續傳來,逆(李)彌殘部約有壹萬多人蠢蠢欲動,將於近期分路竄犯國境。”李老是陜北人,雖然到南方生活大半輩子,但是壹口鄉音未改,壹如既往地把“李”說成“逆”,“我”說成“額”。
“4月,第壹股敵人在南路出現,來勢很兇,目標是猛連,景洪。額(我)們開始判斷有誤,註意力被吸引到南路。加上下面個別部隊領導犯了急躁主義,以為這是敵人主力,想立頭功,沒有等把他們完全放進來就沖上去,違背軍區首長誘敵深入的指示精神。敵人本來就是佯攻,妳壹打,他頭就縮回去,跟妳玩‘敵進額(我)退’的遊戲。直到4月下旬,敵人主力才真正出現,他們的目標是臨滄和思茅。當時分析,敵人還有沒有更大的作戰意圖?他們只是壹般性騷擾還是真的打算在雲南建立根據地?他們還有沒有別的戰術目標?
“軍區首長多次指示:不要性急,把敵人放進來,放深入壹些。放長線釣大魚嘛。額(我)們采取壹些主動措施誘敵深入,希望敵人再向東前進,最好是臨滄和鳳慶,這樣額(我)們就有把握關上門,把他們全殲,除去境外壹個毒瘤。但是敵人很狡猾,始終不肯上當,相持兩個月,敵人時進時退,逆(李)彌龜縮在耿馬、雙江壹帶,也搞發動群眾那壹套,當然是欺騙蒙蔽覺悟不高的群眾。”
我問:“妳們後來查清楚敵人意圖了嗎?”
李老笑著說:“反攻大陸唄。蔣介石要他反攻,逆(李)彌又不能違抗命令,可是他反攻又怕被額(我)們消滅,所以就來個消極怠工。”
我說:“從客觀上講,李彌反攻起到什麽作用沒有?”
李老沈思片刻回答:“恐怕不能說壹點作用也沒有。為防備國民黨殘部竄犯邊疆,中央軍委把原定入朝作戰的第某某、某某軍都留下來,這就是壹種牽制作用。另外逆(李)彌把滇西、滇南分散的蔣殘匪和反共勢力糾集起來,起到了壯大隊伍的作用。”
另壹位離休老人彭荊風是我尊敬的前輩作家,老人看上去面色有些倦怠,但是精神尚好,思路敏捷,記憶力驚人。他對過去發生在西南邊陲的幾乎所有事件都了如指掌,說起話來仍然帶有江西老家口音,語氣果斷勿庸置疑。
“1951年我在連隊當文化教員,那時候我還是個十八九歲的小青年,投身革命隊伍,熱情似火,整天不知疲倦。國民黨竄犯大陸,雲南邊疆是重點地區,當時打了那場很有影響的耿馬、雙江戰鬥。我並沒有直接參戰,而是後來接觸了許多戰鬥英雄,又深入部隊和臨滄地區采訪。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火熱的生活孕育了我的創作靈感,所以我壹口氣寫出了兩個電影劇本,還有壹些別的作品。”
我問:“您認為您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真實嗎?”
彭老毫不遲疑地回答:“是的,至今我仍然堅持這樣認為。當時剛剛結束內戰,民心向往和平安定,渴望建設家園,共產黨有充分的信心挑起建設國家的重任。國民黨反攻大陸是壹種不得民心和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舉動。”
我說:“根據我的采訪,1951年的戰鬥沒有達到全部消滅敵人的預期目的,是否可以認為是壹場不成功的軍事行動呢?”
彭老連連搖頭道:“這樣看法是片面的,很不客觀。邊疆保衛戰雖然只斃俘壹兩百名敵人,看上去不能同解放戰爭中任何壹場勝利相比,但是在政治上的影響和意義卻十分巨大,不僅有力保衛了邊疆,支持抗美援朝,而且徹底粉碎了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妄想,起到警戒壹切敢於來犯之敵的作用。李彌縮回金三角,從此再也不敢大規模竄犯邊境。這壹仗還應該包含壹些有益的軍事啟示:境外之敵已經不是壹兩年前的國民黨正規部隊,他們正在和還將發生變化,熱帶叢林作戰是他們最大的特點,應當予以密切關註。可惜當時大家都意識不到這壹點。當然也不能怪誰,人的認識總是隨著事物的變化而逐步提高……這個教訓直到十年後的勘界警戒作戰才表現得淋漓盡致。”
我把話題轉向境外。我告訴彭老,現居金三角的許多國民黨將領都對1951年春天那場反攻雲南的戰鬥有所反省。比如李崇文將軍說,因為政治仇恨蒙住眼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實在是件可悲的事情。
彭老笑笑說:“如果他們都像現在,能回大陸親眼看看,他們就不會去做那樣自欺欺人的所謂反攻夢想。”
最後壹個話題是關於對金三角國民黨殘軍政策。彭老說據壹本公開出版的資料披露:鑒於金三角國民黨軍殘軍同臺灣當局在組織上已無隸屬關系,殘軍人員大多在當地安家,取得所在國“居留證”,有人已加入外國籍,不再從事危害祖國的活動,1981年根據中央和總政指示,停止對這股前國民黨武裝的工作。等等。
許多老人都說,我出生前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怎樣壹個生機勃勃和萬眾歡騰的年代啊!壹提起那段日子,我父母的神情立刻變得年輕起來,因為那時候他們正好年輕,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年輕的日子誰不珍藏在心呢?
舊政權像昨天的太陽已經落下山去,新時代像初升的朝陽剛剛升起來,新舊交替的時代變革給年輕人帶來許多新的選擇,許多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人人都有機會改變自己,改變未來,在壹個給人帶來變化的年代,人人都因為充滿希望而朝氣蓬勃。
我壹位堂伯父說:“那時候,報紙天天都有勝利消息,廣播裏朝鮮戰場天天都在打勝仗,美國人變得跟兔子壹樣只會逃跑。解放軍進軍西藏,大剿匪,農村土改,鎮壓反革命等等。人人都在歡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大街上秧歌隊鑼鼓喧天,歡送青年到隊伍裏去。總之那是個火紅的年代,人人都有緊迫感,形勢逼人,時代像滾滾車輪,妳壹猶豫就掉隊了。”
我的嶽父,壹位享受離休待遇的老人,他的經歷更是大起大落。本來到美國留學的飛機票已經買好,因為聽從組織召喚(他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進步組織),毅然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轉而投身保衛城市和學校的鬥爭。後來他被分配到政法戰線工作,是我們這座城市裏資格最老的法官之壹。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從此命運壹落千丈,直到改革開放,經過種種努力才爭取來壹個離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的父親就顯得比較被動,他壹心只想當科學家,對政治不感興趣,我認為這起碼是覺悟不高的表現。父親說:“那時政府號召年輕人參軍,抗美援朝,學習文化。大學裏也招兵,不少同學上著課就不見了,原來是參軍走了。”
我問:“您為什麽不去參軍呢?那時候參軍多光榮,我們也好落個革命軍人的光榮出身呀。”
父親回答我:“要是我打仗死了,就什麽也沒有,現在至少我還留下妳們這幾個孩子呀。”
我說:“當時您大學畢業準備幹什麽呢?”
父親回憶說:“妳爺爺打來電報,要全家都到加拿大定居,後來沒有走成,我也跟著留下來。”
我心中掠過壹陣激動,原來我們險些就成為令人羨慕的海外華僑啊。我幾乎絕望地嚷起來:“當時您為什麽不走?爺爺不去,您壹個人走啊,拿出您當年背著家裏參加遠征軍到印度打仗的勇氣來。”
父親望著遠處說:“我回到妳爺爺的工廠做練習生。是妳爺爺決定的。”
父親辛勤工作壹輩子,歷經人生坎坷,八十年代以副教授職稱退休。我幾乎有些恨我的爺爺,是他老人家扼殺了父親和我們壹家人的光明前途。後來發生的事情我知道壹些,爺爺工廠沒能堅持多久,因為私有化很快被公有制進程取代,爺爺變成壹堆被稱為“股票”的廢紙擁有者。他老人家民國初年創辦中國“裕華”、“大華”紗廠,是著名的民族實業家,仙逝於1960年。
我美麗的母親在學生時代向往參軍,當壹名光榮的誌願軍或者解放軍的女文工團員。那時候她只有十七歲,還在成都華美高中念書,是那種充滿幻想的花季少女。她的不少女同學都因為走上革命道路,穿上軍裝,成為跳舞唱歌的文工團員然後嫁給首長,成了很有級別的高幹夫人。我說:“您為什麽沒有去實現自己夢想呢?依您的條件,走這條道路應該不成問題呀?”
母親有些害羞地笑笑說:“當時部隊到學校招文工團員,我記得很清楚,說是到廣州去。首長第壹個批準我,馬上就讓上車出發。我說我得回家說壹聲,我最放心不下妳外婆。結果這壹回家就再也沒有出來……都怪妳外公自私。他把我當成搖錢樹,當兵還搖什麽錢呢?”
我說:“您為什麽不反抗呢?白毛女都能反抗黃世仁,您還不能反抗壹個外公嗎?您壹反抗,我們這些後代不就走上另外壹條道路了嗎?”
母親嘆口氣說:“這都是命啊!女孩子,遲早要嫁人,反抗有什麽用?”
我覺得像母親這樣的資產階級小姐基本上沒有什麽希望,沒有反抗精神,也沒有革命理想和堅定信念。但是連她都有過突圍沖動並險些獲得成功,這說明革命形勢已經像春風壹樣深入人心催人奮進。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關於本世紀五十年代初壹個新政權建立時的精神面貌。國民黨舊政權的陰影正在消失,共產黨領導的新時代剛剛開始,年輕的共和國因為贏得大多數民眾擁護而生氣勃勃,兵強馬壯,顯示出敢於同壹切帝國主義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在這樣壹個年代,任何人復辟舊政權和反攻大陸的夢想都是註定要失敗的。
2
許多年前,我在雲南邊疆度過壹段漫長而且難以忘懷的知青歲月。那時候我們兵團知青分布在千裏邊防線上,壹手拿槍,壹手拿鋤,執行祖國賦予我們屯墾戍邊和接受再教育的光榮任務。我所在的團(後改為農場)地處中緬邊境,地名叫隴川,全縣人口不足萬人,以致於許多知青到了目的地他們的父母還沒有從地圖上找到那個叫隴川的小地方。
其實我們守衛的這片國土上還是出過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出過全國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女英雄徐學惠。八十年代以後的年輕人已經不大聽說這個名字,但是在五六十年代,這個名字幾乎婦孺皆知,其知名度與江姐、劉胡蘭、丁佑君、向秀麗等女先烈並列,惟壹的區別是先烈死了,徐學惠活著。
徐學惠是隴川縣銀行,準確說是我們農場壹個小儲蓄所營業員,那個小儲蓄所離我們連隊只有三裏地,在糖廠水庫邊上,而我們農場另壹個後來成了有名氣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們連隊也離那座水庫不遠。我們很多知青都到那個小儲蓄所存錢,不是錢用不完,是怕花光了回不了家。
徐學惠事件發生在五十年代的壹個夜晚,當時年輕的徐學惠只有不到二十歲,未婚,是否有對象不詳。壹群國民黨殘匪從國境對面的“洋人街”過來搶劫儲蓄所,徐學惠死死抱住錢箱不松手,以致於殘暴的匪徒竟把她的雙臂活活砍下來……
這是我們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隴川發生的著名事件,這件事甚至驚動當時的黨中央和毛主席。徐學惠出名後受到黨和國家關懷,調到昆明,裝上假肢到處給青少年作報告。“文革”期間受“四人幫”拉攏當上省革委副主任,相當於副省長,終於晚節不保銷聲匿跡。
當我在金三角采訪反攻雲南的國民黨殘軍,提及名噪壹時的徐學惠事件,他們都搖頭否認,不肯承認罪行,好像個個都很無辜的樣子。我理解他們的心情實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認南京大屠殺,好像那幾十萬人都是自殺的。徐學惠會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來嗎?
國境對面那個外國小鎮叫“洋人街”,據說是國民黨的據點,後來我才知道,“洋人街”是聯合國禁毒署列入名單的世界毒窩之壹。不過當時金三角惡名遠沒有像今天這樣令人談毒色變,政治任務高於壹切,所以我們屯墾戍邊的主要任務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蔣殘匪竄犯邊疆。
“蔣殘匪”是個定義不詳的歷史符號,從前我常常在電影中看到他們,就是那種經過藝術加工的獐頭鼠腦的壞人。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這個符號就變得很不具體,比方夜裏突然升起壹二顆信號彈,出現幾張反動傳單,傳說某地橋梁水庫遭到破壞,生產隊耕牛被毒死,等等。開始知青警惕性很高,深夜壹吹集合哨,大家趕緊起床執行任務,褲子穿反也顧不得,壹心指望抓住敵人當英雄,有人因此掉進溝裏摔斷腿終身殘廢。久而久之,白天勞動,晚上備戰,人累垮了,敵人卻連鬼影也沒有見壹個。幸好後來上級傳達指示,說敵人搞疲勞戰術,我們從此安心睡覺不再理會。
我們勞動的山坡對面就是今天令人談毒色變的金三角,國界是壹條不足兩米寬的小河溝,兩邊山頭上都覆蓋著郁郁蔥蔥的森林。我們男知青常常站成壹排,壹齊把尿撒過國界,戲稱“轟炸金三角”。“洋人街”坐落在我們連隊對面山上,肉眼能看見許多鐵皮房子掩映在綠樹叢中,太陽壹升起來,那些房頂就閃閃發光,像小時候看過的童話故事,令人遐想無限。但是指導員嚴肅指出,殘害徐學惠的國民黨殘匪就是那裏派出來的。敵人亡我之心不死,他們每時每刻都在企圖復辟,妄想反攻大陸。還鄉團回來了,我們就會千百萬人頭落地!
邊疆七年,我的知青生活中像風壹樣刮過許多有關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傳說。比方五十年代,某寨子吊死我兩名英勇的偵察員。某路口,敵人支起大鍋將我方傷員(或者幹部,或者農會主席)活活煮死。我沒有想到的是,許多年以後自己將走進這些躲在金三角也就是歷史帷幕後面的人群中間,成為壹段特殊歷史的揭秘者和書記員。
另壹件事情是,八十年代末我重返農場,改革開放,邊疆發展邊貿,我終於有機會走進國境對面那座像乩語壹樣神秘邪惡的“洋人街”,了卻壹樁心願。其實我看到這是座很平常的緬甸小鎮,低矮的鐵皮屋頂,飛舞著蚊蟲蒼蠅,充斥著垃圾和熱帶氣息的骯臟街道,做生意的人群和騾馬散發出令人惡心的汗酸味,毒販公開向遊客兜售毒品。在壹座大房子跟前,當地人告訴我,這是從前的漢人(國民黨)情報站,廢棄多年,現在成了教堂。我駐足傾聽,果然聽見有嗚嗚呀呀的管風琴聲從教堂的窗口飄出來。
我重重舒壹口氣,走出歷史陰影,走到明亮的陽光下。
3
許多金三角老人回憶說,1951年,反攻命令壹下達,在國民黨官兵中引起壹片熱烈歡呼。許多人流出激動的眼淚,對空鳴槍,扔帽子,還有人幹脆蹲在地下嚎啕大哭,好像壹群被告之可能回家的流浪孩子。
我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曾經對此深感困惑。因為我不明白,這些丟盔卸甲的國民黨殘軍難道沒有壹點自知之明,他們憑什麽相信反攻大陸會成功?他們難道忘記僅僅壹年前,他們是怎樣從大陸狼狽逃出來的?他們難道真的不知道他們的對手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強大,而他們自己不過是壹群虛張聲勢的流寇?
但是當我走進五十年前這群失敗者中間,我的心情豁然開朗,因為我並不費力就找到答案所在。
在泰國北部城市清萊,壹位參加過反攻雲南的前國民黨將軍面對來訪的大陸作家,極為感慨地嘆息道:“我們同共產黨打了幾十年仗,還是不了解共產黨。現在來看,反攻大陸完全是壹廂情願的事,因為我們根本不了解大陸,總認為人民站在我們壹邊。如果人民站在我們壹邊,國民黨怎麽會失敗呢?……弄明白這個簡單道理,我們用了五十年時間。”
在金三角小鎮回海,另壹位已經加入泰國籍的華僑老人平靜地說:“什麽叫鴻溝,什麽叫仇恨?國民黨被趕出大陸,趕出國境,這叫仇恨。廣大官兵只能聽見臺灣宣傳,相信壹面之辭,這是鴻溝。臺灣宣傳說,共產黨如何殘暴,屠殺人民,共產共妻,老百姓怎樣生靈塗炭,人民如何盼望國軍回去解救他們,只要妳們反共救國軍壹到,人民立即就會群起響應,以起義和戰鬥歡迎妳們,共產黨政權立刻就會像太陽下的冰雪壹樣土崩瓦解……妳知道蔡鍔北伐的故事,他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我們把李主席看作金三角的蔡鍔,反攻雲南就是又壹次北伐。如果我們有可能像現在這樣常回大陸看看,誰還會相信那些幼稚可笑的政治謊言呢?問題在於,當時我們都相信了,而且深信不疑。”
我感興趣的另壹個問題是,如果廣大官兵被蒙蔽,作為國民黨主帥的李彌,他相信自己會成為壹個新的蔡鍔麽?他有能力改變歷史命運,反攻大陸成功麽?如果他不相信,他為什麽還是要全力啟動這場大陸解放以來惟壹壹次大規模竄犯大陸的軍事行動?他怎樣扮演這個兩難的歷史角色?
根據不少老人的敘述,我漸漸看見將近半個世紀前,反攻雲南的國民黨主力在孟薩集結完畢,李彌親自將部下兵分兩路:壹路大張旗鼓向東佯攻景洪,擾亂共軍視線,另壹路主力則在緬北山區隱蔽行軍,直到四月下旬才抵達壹座地名叫做巖城的佤山。巖城古稱永恩,界河對面就是雲南西盟縣城。
我對此感到疑竇叢生。作為壹個軍事指揮官,“兵貴神速”永遠是壹條戰術要義。可是李彌部隊似乎並沒有緊迫感,他們就像遊山玩水,幾百裏路居然走了兩個月時間。我向武老請教,前國民黨幕僚回答說:“行軍就是行軍,沒有人拖延時間。”
我攤開地圖向他指出:“可是這樣壹條路線,妳們居然走了整整兩個月!那麽妳們都幹些什麽事情?”
他態度甚為安詳地說:“發動群眾,擴大影響呀!我們每到壹個地方,就動員青年當兵,建立反共遊擊武裝,宣傳三民主義等等。”
我說:“妳們不怕暴露意圖,不怕解放軍偵察到妳們行蹤?”
武老笑笑說:“只有傻瓜才會相信,我們那區區幾千人能反攻雲南。美國人在韓戰中吃緊,臺灣有精兵百萬尚難自保,我們能起多少作用?”
我眼睛壹亮,追問道:“李彌真是這樣想的嗎?既然明知道不可為,為什麽還要反攻雲南?”
武老點頭贊嘆道:“這就是李主席英明過人之處啊!古人雲,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嘛。”
我開始有些明白,李彌其實是在下賭註,只不過他押的寶不在大陸,也不在臺灣,而在美國人身上。
緬北山區原本沒有國民黨勢力,李彌大軍壹路走,壹路招兵買馬,幾乎毫不費力就把沿途土司山官統統招安,封了許多縱隊司令支隊司令,最小的也是上校獨立大隊長,反正只要給槍給錢,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部落酋長封建頭人決沒有不肯依附的道理。李彌對此很滿意,向臺灣發電稱,反共救國軍實力擴大好幾倍。
巖城是座方圓百裏的大山,為佤族山官屈鴻齋的領地。屈鴻齋號稱“巖城王”,這個土皇帝卻不是佤族,他是雲南漢人,犯殺人罪逃過國境避難,做了佤族山官的上門女婿。山官沒有兒子,由他繼承世襲領地。李彌派人做策反工作,送了許多銀元和槍支,委任他為少將縱隊司令。事實上這種收買戰術幾乎百戰百勝,比如從前的殺人通緝犯屈鴻齋,壹夜之間舊貌換新顏,坐在家裏就白白當上將軍,這樣的好事上哪裏去找?山大王屈鴻齋簡直被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砸昏了頭,立刻豎起反共救國軍旗幟,積極充當反攻大陸的前鋒。
4月,擔任佯攻的部隊來電告急,說共軍主力來勢兇猛,隊伍被黏住撤不下來,如不及時撤退,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也就是說,李彌在路上慢騰騰地磨蹭,反攻大陸的計劃尚未執行就有可能流產,這樣至少沒法對臺灣交差。當然還有壹個更加重要和隱秘的原因,這是李彌全部計劃的核心,如果反攻流產將危及這個計劃的實施,所以李彌突然變得著急起來,倉促變更部署下達命令。
前衛師長李國輝奉命淩晨向滄源縣城發起進攻。
4
這是個久旱無雨的黎明,雲貴高原的紅土地因為缺乏水分而變得蒼老,壹層薄霧如碳灰般將天地籠罩,河流奄奄壹息,巖石蒙上壹層灰。在這個霧蒙蒙的背景下遠遠望去,巨大的朝日剛剛升起,好像壹枚被踩扁的紅鴨蛋,坐落在山巒間的滄源壩子猶如涸轍之鮒,張開幹渴的大嘴等待壹天漫長的熱帶幹風和太陽的無情煎熬。
在這個旱季即將走到盡頭的早晨,國民黨先遣部隊越過國境線,對滄源縣的前哨陣地蠻宋發起攻擊。解放軍駐蠻宋壹個排,以石頭碉堡的哨所為陣地進行頑強抵抗,戰鬥隨即展開。錢運周指揮特務大隊和士兵將哨所團團包圍,雖然國民黨官兵都知道共軍只有壹個排,等於壹顆釘子,而不是匕首,但是他們的行動還是十分小心謹慎。因為這裏畢竟是大陸,對手不是只會朝天放槍的老緬兵土司兵,誰能說釘子不能致人死命呢?
青黑色的碉堡像壹頭怪獸,披著壹層淡薄的晨霧蹲在山坡上,黑洞洞的槍眼猶如深不可測的眼睛,讓人感到心驚肉跳。壹群色彩斑斕的印度虎皮鸚鵡被士兵腳步驚飛起來,它們在亞熱帶旱季幹燥的空氣中努力振動翅膀,把誇張和不安的尖叫聲撒得很遠。錢運周從望遠鏡裏看見碉堡外圍有許多障礙物,樹叢中有新掘的戰壕,解放軍隱蔽得很好,看不見人影晃動。
碉堡越來越近,只剩下幾百米距離,敵人還是沒有動靜。錢運周感到背上有些發冷,這是壹場正規戰,不是打土匪,作戰雙方是較量幾十年的老對手,彼此熟悉得如壹家人。共軍好像有意折磨他們,越是保持沈默,進攻者越是緊張,誰都知道,距離越近,打得越準,國民黨士兵快把頭埋在地上,雖說敵人只有壹個排人,可是槍響起來,誰又擔保自己腦袋不被先打穿幾個窟窿呢?……
終於“砰”的壹響,共軍開槍了!槍聲使人精神壹振,快要凝固的空氣嘩啦破碎了。這壹槍實在太差,像走火,因為子彈並沒有射向人體,而是滴溜溜地鉆進泥土裏去了。所有人都同時松了壹口氣,就像捆綁在身上的繩索松開來,他們從地上擡起頭來張望,看見解放軍陣地上冒出壹縷細細的青煙,可以想象那是個驚慌失措的新兵。於是進攻壹方士氣大振,嗷嗷叫著兇狠地彎腰沖鋒。
形勢對防守壹方不利,盡管他們頑強抵抗,但是雙方畢竟力量懸殊太大,所以第壹輪進攻下來,國民黨殘軍占領外圍陣地,把剩下的解放軍全都逼進碉堡裏去了。
晨霧漸漸散開去,太陽露出臉來,把紅通通的光輝斜灑在戰場上。碉堡四周躺著幾具屍體,他們看上去不大像死人,臉上泛著紅光,像心滿意足的醉漢。錢運周讓士兵喊話,繳槍不殺,國軍優待俘虜,碉堡裏面有人大聲回罵。這時李國輝也上來了,他聽出對方是個河南口音,就對錢運周苦笑道:“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媽的!給我轟老鄉幾炮!”
炮聲壹響,對方沈默下來,解放軍當然明白炮擊對他們意味著什麽。炮彈將不結實的碉堡掀開壹角,石墻炸塌,壹些殘肢斷體被氣浪血淋淋地拋到陣地外面來。國民黨官兵歡呼起來,他們被勝利的炮火所鼓舞,挺直腰來進攻,解放軍這回是真的完蛋了,好比壹頭死老虎,誰先沖上去誰揀勝利果實。
頑強的解放軍還有壹挺機槍在廢墟中射擊,零落的步槍也向進攻者表達誓死不降的決心,進攻人群吶喊著,像潮水壹樣撲向孤零零的石頭碉堡。這是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勝利眼看就要得手,敵人馬上就要被全殲,反攻大陸首戰告捷的電報立刻就要飛向臺灣,國民黨打了許多年敗仗,逢共必敗,這回他們要向老對手劃壹個精彩的句號。但是這時候壹個意外發生了,他們身後突然飛來壹陣劈頭蓋腦的手榴彈,就像晴空萬裏下起冰雹,手榴彈的猛烈爆炸打亂進攻的隊伍,連督戰的李國輝也險些被壹塊彈片擊中。
壹臺精彩救援的好戲就在國民黨反攻大軍眼前搶先上演。大約壹百多名機動靈活的解放軍援兵(其中部分民兵)從側翼發起虛張聲勢的襲擊,壹下子將敵人打懵了頭,與此同時,困在碉堡裏的解放軍迅速撤下陣地突圍。他們配合得十分默契,壹進壹退,壹張壹弛,就像給國民黨官兵上軍事課壹樣。
李國輝眼睜睜看著共軍像孫悟空壹樣逃出他的手心,這壹仗打得無比窩囊,煮熟的鴨子居然在他面前飛走了。他咬牙切齒地說:“給我追上去,壹直追進縣城。小錢,妳帶壹團人繞過縣城,切斷敵人退路。我要看看共軍再耍什麽花招!”
解放軍並沒有如李國輝所料那樣死守待援,他們在退路被切斷之前主動放棄縣城,朝雙江方向撤退。國民黨軍隊占領滄源縣城,俘虜部分未及撤退的傷兵、民兵和工作隊員。李彌聞訊大喜,迫不及待向臺灣發出戰場告捷電,報告反攻雲南首戰大捷,消滅共軍多少多少,已經切實占領雲南第壹座縣城滄源。雲雲。
5
五十年前的滄源是座只有幾千人口的滇西小縣,不通汽車,所謂縣城也就跟內地壹個小鎮差不多,除縣政府臨時辦公的幾間平房,其余都是民居。七十年代我曾經到過滄源,那時我眼中的小縣城僅有壹家國營百貨商店,壹家國營食堂,壹個小郵電所,和壹條石板鋪成的簡陋街道。聽說九十年代滄源徹底改變面貌,縣城擴大十倍,柏油公路壹直通到省城昆明。
1951年春天,所有重返雲南的國民黨官兵都為勝利欣喜若狂,李彌宣布在縣城舉行壹場慶祝“光復”儀式,他迫不及待地騎著馬,帶領壹群幕僚和臺灣記者越過國境,意氣風發地開進滄源縣城。長官檢閱了入城部隊,國民黨官兵舉行分列式和閱兵式,喊了許多參差不齊的口號,可惜當地居民甚少,因為打仗又逃掉壹些,所以掌聲稀落無人喝彩。
臺灣記者進行采訪,許多官兵流下激動的眼淚,他們說早就盼望反攻這壹天,我們壹定要打到昆明去,打到南京去,光復整個大陸。記者把這些豪言壯語都記在本子上,用電臺發回臺灣,還附上傳真照片,說明國軍官兵士氣高昂所向披靡。
李彌視察縣城時險些被壹發偷襲的子彈擊中,他身後壹個幕僚做了替死鬼,原來是滄源縣民兵大隊還在山上抵抗。民兵大隊長是號稱“巖帥王”的當地佤族山官田興武,他同時還擔任共產黨滄源縣長,本來經過秘密策反,田興武已經答應裏應外合消滅共軍,不料戰鬥打響,他又出爾反爾站在共軍壹邊戰鬥。李彌很惱火,叫“巖帥王”的親戚“巖城王”去招降,這才弄明白佤族山官有顧慮,怕國民黨不成氣候,搞不好落個雞飛蛋打的下場。於是李彌決定放下架子,親自同田興武談話。可憐佤族山官壹輩子沒有見過比團長更大的漢人軍官,他甚至連壹百公裏外的臨滄城也沒有去過,所以當大名鼎鼎的國民黨省主席親自同他談話,這位立場不穩的山官嚇得連漢話也說不清楚,結結巴巴像個小學生。他本是個世襲的部落首領,被中國歷史劇變的潮流所挾裹,身不由己地卷入階級鬥爭的激流旋渦中,所以他就沒法不像個陀螺壹樣左右搖擺。李彌當然看出田興武不是個人物,他只用了不出壹袋煙工夫就說服他倒向國民黨壹邊。李彌當場委任他為上校支隊長,然後將他和他的四百多個佤族民兵派到戰場去打頭陣。
俘虜沒有得到寬大。他們多數是工作隊員,有人負了傷,打著赤腳,還有壹個女俘虜,很年輕,戴著眼鏡,據說是大城市來的大學生。他們來不及跟上部隊撤退,也沒有戰鬥經驗,對於階級鬥爭的嚴酷性估計不足,因此他們成為這些反攻倒算的國民黨同胞的復仇對象。我在滄源采訪曾聽當地人控訴國民黨令人發指的暴行,其中最驚心動魄的壹件,就是這些滅絕人性的國民黨匪徒在滄源城裏支起大鍋,將水燒開,把俘虜和傷兵扔下鍋去煮。當時的情形不難想象,開水翻滾著,冒著滋滋的水蒸氣,許多人圍觀,發出快樂和滿足的哄笑,俘虜捆得像粽子,但是那不是粽子,是活人,女大學生!這幅殘酷的畫面壹直留在我的腦子裏揮之不去,我曾為那位不知名的女大學生的悲慘命運暗暗揪心,悄悄垂淚。後來我在金三角質問當時參加反攻的國民黨官兵:“妳們這樣做,不是跟日本人差不多嗎?”
他們回答:“對不起,我保證我所在的部隊沒有發生這種暴行……槍斃俘虜的事是有的,但是煮活人沒有聽說過。”
我氣憤地說:“難道是別人造謠,誣陷妳們不成?”
他們安靜回答:“可能因為仇恨太深,彼此都會有壹些過激言論和誤解。”
這回輪到我無話可說。我只好問:“現在……還有仇恨嗎?”
他們搖頭說:“都是中國人,過去的事想來很內疚。不管什麽黨,只要妳把國家治好,中國強大,我們就擁護妳。”
反攻滄源的初步勝利鼓舞了李彌,他下令乘勝進軍,壹路由李國輝率師進攻耿馬和雙江,另壹路由錢運周指揮進攻西盟和瀾滄,起側翼屏護作用。“巖帥王”田興武決心將功折罪,帶領他的民兵沖在前面打頭陣,解放軍兵力薄弱,連連後退,滇西防線很快被擊破。國民黨殘軍相繼占領四座縣城,並在城頭升起青天白日旗幟。這時大批守候在境外的馬幫蜂擁而至,他們像螞蟻搬家壹樣把這些小縣城裏可憐的百貨商店、儲蓄所、糧站以及壹切可以搬走的財產馱上馬背,然後源源不斷地運往金三角。這種盛況在當地持續了壹段時間,絡繹不絕的馬幫很有耐心地將上述幾座縣城搬成空城。
對於兵敗大陸的臺灣國民黨來說,他們太需要勝利,太需要精神鼓舞了,勝利是壹道美味大餐,而他們是壹群饑不擇食的餓漢。於是臺灣島上所有報紙電臺壹齊歡呼滇西反攻的偉大勝利,好像他們明天就要返回南京壹樣。軍政要員頻頻發表講話,政工部門組織民眾上街遊行,商會財界出資募捐,經過壹番沸沸揚揚地炒作,李彌頓時身價倍增,從壹個坐冷板凳的光桿司令變成家喻戶曉的國軍英雄,他儼然成了共產黨的克星,戰無不勝的二戰名將蒙哥馬利或者巴頓將軍。
臺灣的勝利歡呼還有壹個苦心,那就是做出姿態給美國人看。當時美國人在朝鮮戰場陷入苦戰,巴不得看到共產黨後院起火天下大亂,如果李彌們壹路高歌挺進昆明,共產黨豈不是兩面受敵首尾不顧麽?朝鮮戰場的局面不是很快會發生變化麽?蔣介石這樣做等於提醒傲慢的美國佬:妳們與共產黨打仗離不開我們國民黨,離不開臺灣!
然而就在臺灣和美國盟軍期待李彌勝利捷報頻傳的時候,李彌卻下令反攻隊伍在耿馬縣城停住腳步,壹住就是三個月。
6
耿馬縣城以東四十公裏,有壹塊山間平地叫猛撒,因為是半山腰,沒有水源,所以也沒有人居住。據說知青到來前幾十年,這裏森林茂密,是動植物的樂園,後來遭遇大煉鋼鐵,再後來伐木開荒,到處成了梯田,水土流失嚴重。當時我的同學王仕陸被分配到猛撒農場插隊,番號是建設兵團第二師第八團,他興奮地告訴我,八團居然有座飛機場!我譏笑他,妳們八團知青回家探親不是可以乘飛機了嗎?他說是座報廢了的機場,野戰機場,也許還能起飛戰鬥機。我說莫非妳們八團的橡膠樹需要空軍保衛?他說妳別笑,都是真的。抗戰時期,美國盟軍為了保衛駝峰航線,對滇緬日軍實施有效打擊,曾在猛撒秘密修建了壹座簡易野戰機場。機場只有壹條砂石跑道,幾間簡易棚屋,僅供小型戰鬥機臨時起降。機場即將完工之際,太平洋傳來日軍投降的勝利消息,機場於是尚未啟用便荒蕪下來。後來我查閱史料,同學說得不差,基本上與歷史吻合。
1991年我為寫作《中國知青夢》專程到猛撒采訪,果然看見那座荒蕪的飛機場。機場平整如故,沒有樹,跑道上長滿荒草,像座天然的足球場。
但是當我的視線投向1951年春天,李彌命令他的反攻部隊停在耿馬、雙江壹線按兵不動時,我註意到他同時占領了這座廢機場。國民黨殘軍在廢機場四周布下重兵,我從軍事地圖上看見,李彌部隊的防衛重心事實上已經轉移到這座沒有人跡的廢機場。另壹個反常的現象是,他們的對手解放軍好像也睡著了,沒有反擊跡象,連民兵遊擊隊騷擾也時斷時續,有氣無力。這就有點像姜太公釣魚,人和魚彼此漫不經心,玩著讓外人看不懂的遊戲。根據偵察報告,解放軍壹個團已經撤退到臨滄,滇西方向沒有大部隊。還有情報說共產黨政府機關也開始向大理撤退。壹些將領和幕僚認為共軍主力被調到朝鮮戰場,後方空虛,正是長驅直入的大好機會,有人甚至樂觀預言,半個月收復昆明,打敗共產黨只是壹個時間問題。好像前途壹片光明,共軍不堪壹擊,需要的只是進攻。
李彌穩坐釣魚臺,不為人言所動,對大好形勢視而不見,根本不理睬部下的焦急心情。他安之若素,每天與幕僚品茗論道,談棋說畫,好像他不是來打仗,而是來遊山玩水壹樣。許多急於打回老家的國民黨軍官都沈不住氣,猜不透老長官葫蘆裏賣的什麽藥,連師長李國輝也蒙在鼓裏,跟別人壹樣幹著急。
糊裏糊塗過了十多天,壹個沒有月亮也沒有烏雲的夜晚,星星在天空閃爍,李彌走出他在耿馬縣城的指揮部,騎上心愛的東洋大白馬,率領壹行部下和隨從直奔猛撒機場。當他們翻過山坳,壹個前所未有的燦爛景象突然像銀河落九天壹樣展現在他們面前。黑夜沈沈,機場燃起熊熊火堆,將山間平地映得如同白晝。士兵戒備森嚴,騾馬集合待命,樹叢中隱蔽著大批民工。不久天空響起隆隆的馬達聲,壹架沒有國籍的美制飛機飛臨人們頭頂,這只黑色的巨鳥在天空低飛盤旋,沈重的呼吸響徹夜空。許多國民黨官兵歡呼雀躍,他們激動萬分,以為幾年前抗戰大反攻的輝煌場面將在猛撒重演:巨大的艙門打開,全副武裝的空降兵和坦克大炮源源不斷地從飛機肚子裏開出來。
可惜時過境遷,飛機只投下幾只降落傘就慌慌張張飛走了。人們找到這些掛在降落傘下面的木頭箱子,箱子裏躺著美國武器和彈藥。不管怎麽說,這也算個期待,美國人沒有來,但是美國武器來了,抗戰八年,大後方不就是靠著美國援助堅持下來的嗎?民工忙碌起來,馬幫將這些從天而降的大箱子分解開來,馱上牲口,然後運回金三角大本營孟薩去。當然這僅僅是個開始,此後兩個月,沒有國籍的神秘飛機常常夜間光臨猛撒機場,將各種各樣的作戰物資空投下來,有次還投下兩名美國情報軍官。值得壹提的是,這些武器大多是美軍二戰中使用過的槍炮,美國人用舊武器支援盟友也不是什麽新聞,何況是無償支援。
直到這時,軍官們開始省悟李彌肚子裏的算盤。有壹天錢運周對李國輝說:“什麽反攻大陸?我看叫做反攻臺灣,或者反攻美國更好。總指揮在同臺灣做交易,我們都是他的道具。”
李國輝嚇了壹跳,連忙制止他說:“老弟,咱們都是軍人,傳出去就是謀反罪。再說長官不依靠美國不行啊。”
錢運周嘆道:“師長,我敢打賭,咱們這輩子是不要指望打回老家了。妳沒見總指揮在積蓄他的家當麽?好容易積攢的家當舍得同共軍硬拼?……唉,反正當兵吃糧,脫了軍裝也餓不死,管他個鳥!”
錢運周的話不幸而言中。當隆隆作響的飛機將裝備壹個標準軍(三萬人)的美式裝備空投下來之後,李彌不是宣布挺進昆明而是立即撤退,將主力部隊從雙江和耿馬縣城撤到國境上,作出隨時準備退出國境的姿態。這真是壹場莫名其妙的戰爭,西線無戰事,大家好像彼此謙讓,而讓戰局以外的人摸不著頭腦。當臺灣和西方輿論大肆渲染勝利,把這場有名無實的反攻雲南炒得沸沸揚揚時,李彌卻讓他的隊伍躺在國境上睡大覺,而他自己為了保險,將指揮部先期撤過國境十公裏。這個謎壹直藏了許多年,直到我在金三角采訪,壹位老者才向我揭開這個謎底:美國要求臺灣開辟第二戰場,臺灣命令李彌反攻雲南,李彌則討價還價要求美國援助武器。最後達成秘密協議,美國人同意援助武器,但是有個先決條件,就是空投地點必須在中國境內,也就是說必須在李彌反攻雲南之後進行。
這場遊戲沒有輸家,各得其所。
戰爭演變成壹場曠日持久的對峙。戰場雙方隔著兩百公裏距離,好像在玩老鼠和貓的遊戲。解放軍稍有動靜,李彌就往後退,解放軍壹撤走,國民黨又恢復原來的態勢。幾個回合下來,大家似乎都在比賽耐性,這就很像壹場沒有裁判的拔河比賽,雙方都在拖延時間,等待對方耐心耗盡。
對峙第三個月,僵局終於被打破,解放軍突然以兩師兵力快速運動,國民黨殘軍本是驚弓之鳥,立即向後撤退。這時壹個更加驚人的情報傳來,令李彌不寒而栗。原來共產黨早已布下天羅地網,壹支神勇的精銳部隊已經神不知鬼不覺穿插到國民黨側翼潛伏起來,只等烏龜把頭伸出來,向前深入壹步,這支部隊立刻封鎖國境,切斷退路,形成關門打狗的局面。從前那些鼓吹反攻昆明的軍官幕僚此時背上出了壹身冷汗,他們暗自慶幸還是老長官英明,沒有利令智昏,否則他們全都做了共軍俘虜。反共救國軍火速撤過國境,為防萬壹,李彌還將總部退過薩爾溫江東岸。
只有不識時務的田興武屈鴻齋們沒能逃脫覆滅的命運。他們本來是部落民族,為歷史潮流挾裹,又為眼前利益誘惑,因此替漢人李彌做了擋箭牌和替死鬼。解放軍封鎖國境,他們像被蜥蜴扔掉的斷尾壹樣,被毫不留情地掃進歷史垃圾堆。
7月,朝鮮戰場傳來和談消息,李彌終於找到借口,迫不及待地下令撤退,於是反共救國軍壹路高奏凱歌喜氣洋洋返回大本營孟薩。李彌不僅收獲了美國援助,而且隊伍空前壯大,總兵力翻了壹倍。
7
1998年初冬的壹天,我踏上飛往雲南省會昆明的航班。揚聲器報告飛經西昌上空時,我突然記起將近半個世紀前那個黑色的清晨,李彌從西昌機場起飛去與他的部隊匯合,但是失敗的命運無情阻斷了他的希望。這位國民黨將軍無法在大陸任何壹處機場降落所以只好只身飛往臺灣。我從壹萬米高空鳥瞰大地,紅土高原像壹只制作粗糙的沙盤躺在我腳下,這只古老沙盤已經存在了億萬年,而我乘坐的飛機則像壹只渺小的流星,在永恒的時間和空間緯度上匆匆劃過。
我的采訪是從原昆明軍區離休幹部李老開始的。1951年李老職務為軍區作戰參謀,參加過制定圍殲國民黨反共救國軍的全部作戰計劃。
“……年初軍區有情報,境外國民黨殘部可能對邊疆地區進行大規模竄犯。到三月下旬,敵情就陸續傳來,逆(李)彌殘部約有壹萬多人蠢蠢欲動,將於近期分路竄犯國境。”李老是陜北人,雖然到南方生活大半輩子,但是壹口鄉音未改,壹如既往地把“李”說成“逆”,“我”說成“額”。
“4月,第壹股敵人在南路出現,來勢很兇,目標是猛連,景洪。額(我)們開始判斷有誤,註意力被吸引到南路。加上下面個別部隊領導犯了急躁主義,以為這是敵人主力,想立頭功,沒有等把他們完全放進來就沖上去,違背軍區首長誘敵深入的指示精神。敵人本來就是佯攻,妳壹打,他頭就縮回去,跟妳玩‘敵進額(我)退’的遊戲。直到4月下旬,敵人主力才真正出現,他們的目標是臨滄和思茅。當時分析,敵人還有沒有更大的作戰意圖?他們只是壹般性騷擾還是真的打算在雲南建立根據地?他們還有沒有別的戰術目標?
“軍區首長多次指示:不要性急,把敵人放進來,放深入壹些。放長線釣大魚嘛。額(我)們采取壹些主動措施誘敵深入,希望敵人再向東前進,最好是臨滄和鳳慶,這樣額(我)們就有把握關上門,把他們全殲,除去境外壹個毒瘤。但是敵人很狡猾,始終不肯上當,相持兩個月,敵人時進時退,逆(李)彌龜縮在耿馬、雙江壹帶,也搞發動群眾那壹套,當然是欺騙蒙蔽覺悟不高的群眾。”
我問:“妳們後來查清楚敵人意圖了嗎?”
李老笑著說:“反攻大陸唄。蔣介石要他反攻,逆(李)彌又不能違抗命令,可是他反攻又怕被額(我)們消滅,所以就來個消極怠工。”
我說:“從客觀上講,李彌反攻起到什麽作用沒有?”
李老沈思片刻回答:“恐怕不能說壹點作用也沒有。為防備國民黨殘部竄犯邊疆,中央軍委把原定入朝作戰的第某某、某某軍都留下來,這就是壹種牽制作用。另外逆(李)彌把滇西、滇南分散的蔣殘匪和反共勢力糾集起來,起到了壯大隊伍的作用。”
另壹位離休老人彭荊風是我尊敬的前輩作家,老人看上去面色有些倦怠,但是精神尚好,思路敏捷,記憶力驚人。他對過去發生在西南邊陲的幾乎所有事件都了如指掌,說起話來仍然帶有江西老家口音,語氣果斷勿庸置疑。
“1951年我在連隊當文化教員,那時候我還是個十八九歲的小青年,投身革命隊伍,熱情似火,整天不知疲倦。國民黨竄犯大陸,雲南邊疆是重點地區,當時打了那場很有影響的耿馬、雙江戰鬥。我並沒有直接參戰,而是後來接觸了許多戰鬥英雄,又深入部隊和臨滄地區采訪。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火熱的生活孕育了我的創作靈感,所以我壹口氣寫出了兩個電影劇本,還有壹些別的作品。”
我問:“您認為您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真實嗎?”
彭老毫不遲疑地回答:“是的,至今我仍然堅持這樣認為。當時剛剛結束內戰,民心向往和平安定,渴望建設家園,共產黨有充分的信心挑起建設國家的重任。國民黨反攻大陸是壹種不得民心和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舉動。”
我說:“根據我的采訪,1951年的戰鬥沒有達到全部消滅敵人的預期目的,是否可以認為是壹場不成功的軍事行動呢?”
彭老連連搖頭道:“這樣看法是片面的,很不客觀。邊疆保衛戰雖然只斃俘壹兩百名敵人,看上去不能同解放戰爭中任何壹場勝利相比,但是在政治上的影響和意義卻十分巨大,不僅有力保衛了邊疆,支持抗美援朝,而且徹底粉碎了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妄想,起到警戒壹切敢於來犯之敵的作用。李彌縮回金三角,從此再也不敢大規模竄犯邊境。這壹仗還應該包含壹些有益的軍事啟示:境外之敵已經不是壹兩年前的國民黨正規部隊,他們正在和還將發生變化,熱帶叢林作戰是他們最大的特點,應當予以密切關註。可惜當時大家都意識不到這壹點。當然也不能怪誰,人的認識總是隨著事物的變化而逐步提高……這個教訓直到十年後的勘界警戒作戰才表現得淋漓盡致。”
我把話題轉向境外。我告訴彭老,現居金三角的許多國民黨將領都對1951年春天那場反攻雲南的戰鬥有所反省。比如李崇文將軍說,因為政治仇恨蒙住眼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實在是件可悲的事情。
彭老笑笑說:“如果他們都像現在,能回大陸親眼看看,他們就不會去做那樣自欺欺人的所謂反攻夢想。”
最後壹個話題是關於對金三角國民黨殘軍政策。彭老說據壹本公開出版的資料披露:鑒於金三角國民黨軍殘軍同臺灣當局在組織上已無隸屬關系,殘軍人員大多在當地安家,取得所在國“居留證”,有人已加入外國籍,不再從事危害祖國的活動,1981年根據中央和總政指示,停止對這股前國民黨武裝的工作。等等。